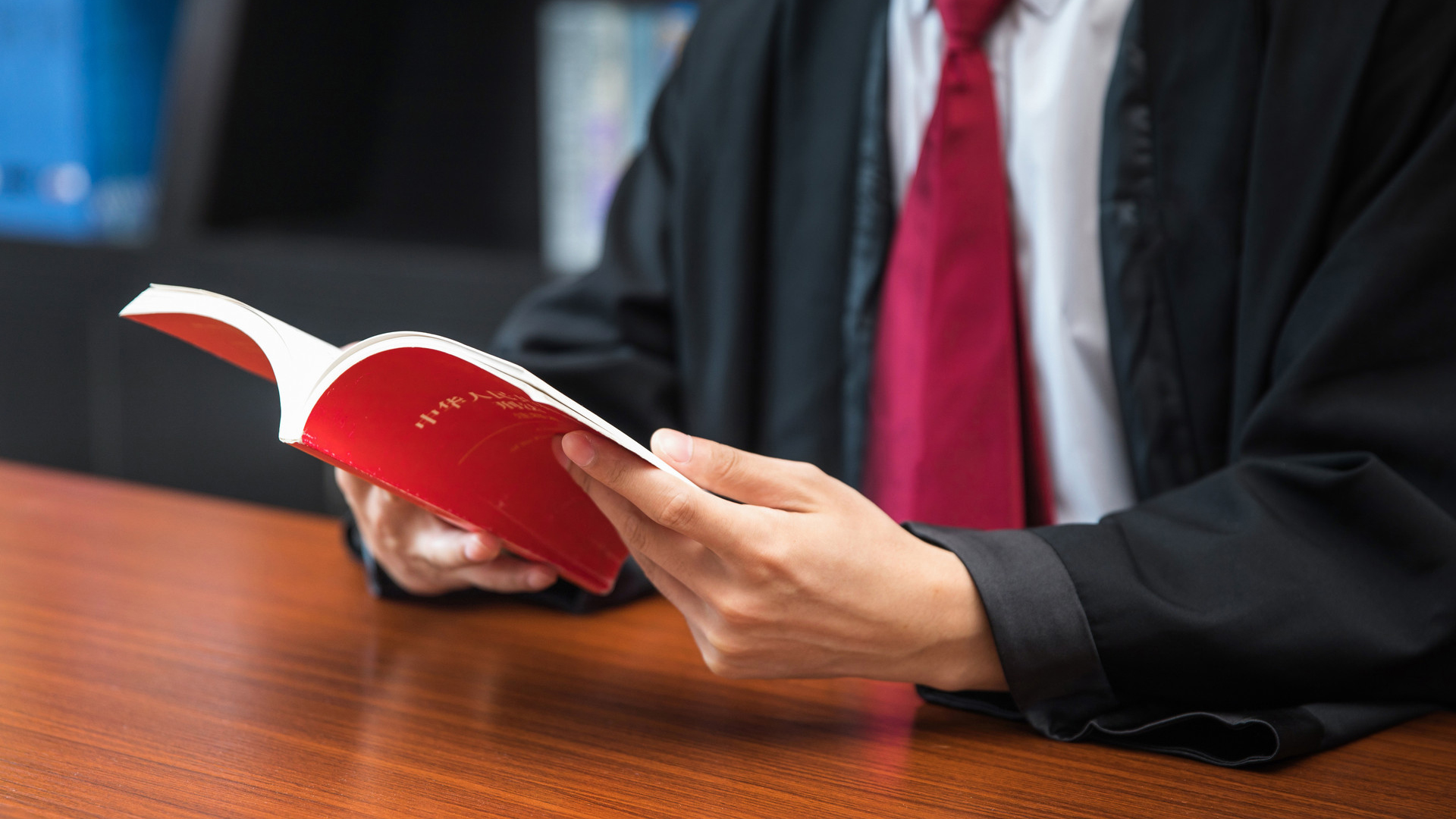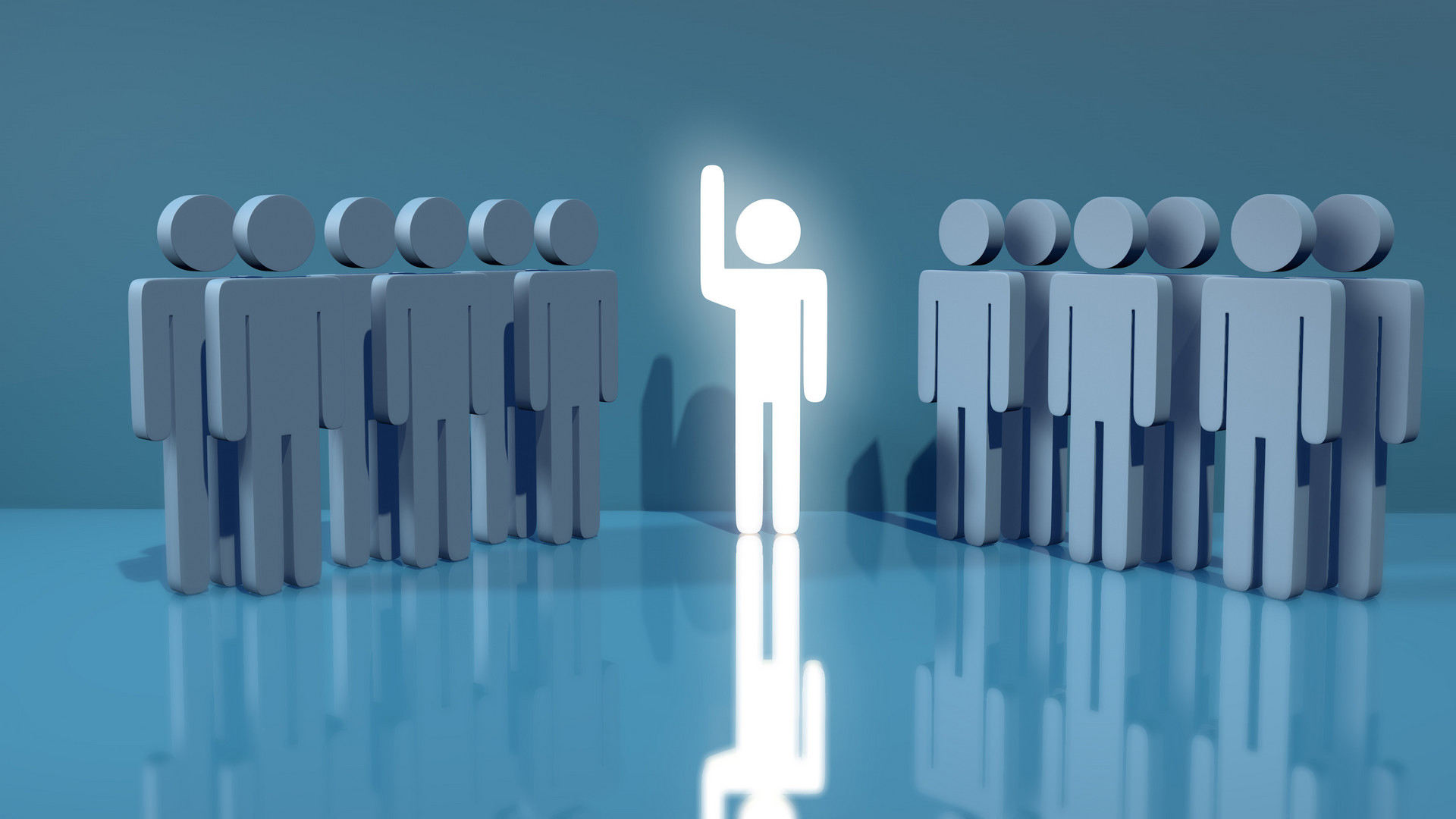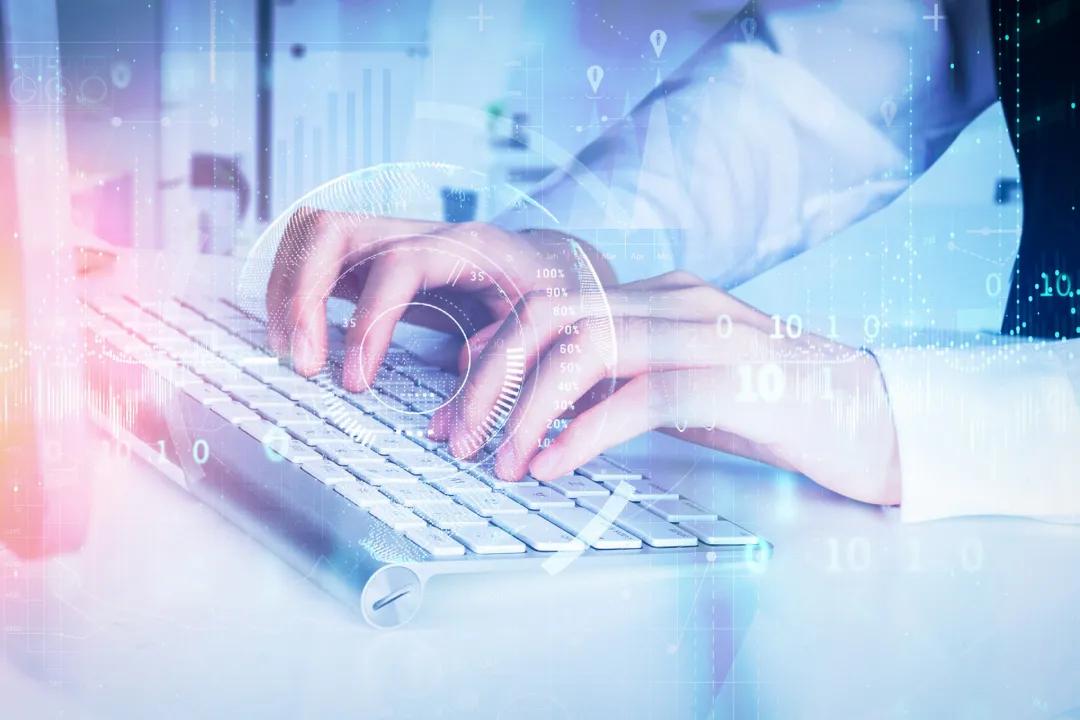法务知道 | 民法典时代,企业如何应对违约方终止合同请求权?
2020-08-17 23:51:37

结合《九民纪要》发布后的首个违约方解除权案例,探讨企业该如何设计合同来预防风险。
文 | 卫新 周徐乐 转自“星瀚微法苑”微信公众号
从《九民纪要》第48条到《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有关违约方终止合同请求权的表述一再改动,给商业社会中的合同履约带来影响。法律是否真正赋予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企业应如何设计合同来预防交易相对方提出的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风险?
本文将从《九民纪要》发布后的首个违约方解除权案例出发,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务经验,为企业修订合同、适应新法变化提出几点法律建议。
1
《九民纪要》后的违约方
解除权第一案
重庆学生小奕,因其优秀的唱跳才艺被某演艺公司选中,两年前受邀来到上海,成为一名接受公司专业培训的练习生。
小奕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替小奕与演艺公司签订了长达11年的《艺人合同》。然而在履行一年多后,小奕便决定继续回到原籍学习,并于2018年8月正式向公司提出解约。
由于双方协商未果,小奕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理由是公司存在教唆未成年人外出喝酒、在节目中抹黑艺人形象和违反教育部有关借读规定等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但审理中法院对于上述事实均未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公司也根据合同履行了相关义务,不构成根本违约,驳回了小奕的诉请。小奕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过程中,适逢《九民纪要》出台,其中第48条规定:
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
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
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
于是,上海市一中院首次适用《九民纪要》第48条违约方起诉合同解除的规定,认为:
第一,小奕为专心学业参加高考而不履行合同,不属于恶意违约的情形;
第二,若继续履行合同,必然影响小奕的学业,进而影响其人生道路发展,对其显失公平;
第三,小奕早已返回原籍就学,合同已近两年未实际履行,且缺乏继续履行的现实基础。
在此情形下,演艺公司仍拒绝解除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二审法院认定小奕符合违约方解除条件,改判合同解除。

2
合同僵局的司法
实践及比较法处理
对于持续性合同中因重大原因变更导致合同履行受阻,有解除权的守约方拒不解除,以致合同陷入僵局的情况,我国立法上原无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常通过将《合同法》第110条第1款第2项的抗辩权解释为“解除权”,予以类推适用;或者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个案进行裁判,破解合同僵局,比如2006年最高法公报的冯玉梅案。但由于欠缺上位法依据,法院为实现个案正义而援引的合同法第110条,在裁判说理过程中显得十分牵强。
对此,我们可以从国外的立法实践中找到借鉴。比如德国法规定了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终止权来化解合同僵局。《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第1款规定:
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可以由于重大原因而通知终止继续性债务关系,无须遵守通知终止期间。在考虑到单个案件的全部情事和衡量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将合同关系延续到所约定的终止时间或延续到通知终止期间届满之时,对通知终止的一方来说是不能合理地期待的,即为有重大原因。
因此,该条款赋予合同当事人在丧失长期关系信赖基础,或继续维持有违诚信原则的情况下,基于“重大原因”终止合同关系的权利。
3
民法典关于破解
合同僵局的立法博弈
弥补上位法空缺,化解合同僵局的难题,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也一直是颇具争议的理论问题。早在民法典一审稿和二审稿时期,“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权利”被置于民法典的合同解除体系之下,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
但是,迫于“违约方解除权”所面临的道德性及正当性压力,立法者不得不在民法典三审稿时删除了这一规定。
等到《民法典》草案上会前夕,该条款被置于第580条第2款重新提交审议。本次调整将该条款续接在原《合同法》第110条之后,体系上属于违约责任范畴,不再局限于对“持续性合同”的调整,并回避敏感的“解除”字眼,改采“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缓和表述。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2)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3)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结合《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立法背景,对照《合同法》第110条和《九民纪要》第48条的规定,我们认为需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民法典一改草案和《九民纪要》使用的“违约方解除”等相关表述,采用“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概念,其法效果有待明确。理论上,“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往后发生效力,无溯及力。对于合同终止前双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否可以适用合同解除对应的法律效果,或者应当适用其他何种法律效果,未予明确。
第二,民法典承继《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强调履行不能的客观事实,《九民纪要》则同民法典一审、二审稿保持一致,还强调“违约方是否恶意”、“守约方是否有违诚信”等履行不能的原因。
第三,《民法典》和《九民纪要》之规定为违约方通过诉讼摆脱债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若不严格限制其法律适用,易将大量非金钱义务通过违约方请求法院终止合同关系的方式,转化为损害赔偿等金钱义务予以替代。

4
合同僵局的现实成因
要理解法律规定背后的逻辑,首先需要思考合同僵局的现实成因。我们认为,造成“合同僵局”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当事人间违约责任约定的缺失
实践中,当事人间对于非金钱义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往往未事先明确。若守约方行使解除权,对方依据合同约定需履行的非金钱义务将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守约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通常难以确切评估或量化,也难以举证证明。因此,拥有解除权的守约方不愿主动解除合同,致使双方陷入合同僵局。
2) 法院对违约责任的法定调整
违约金的适用以填补损害为原则,故法院对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事先约定了高额违约金,考虑到违约行为与实际损失很难对应折算成金钱债务,该违约金仍有被法院调整的可能。如此一来,守约方便丧失了通过行使解除权,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动力。
3) 当事人为摆脱合同展开的利益博弈
有效的合同对于当事人具有同等拘束力,但双方想摆脱合同关系的急迫性并不相同。当违约方急于摆脱合同,手握解除权的守约方便会利用这一点与对方展开利益博弈,迫使违约方妥协并接受己方提出的方案。因此,合同僵局也有可能是商业博弈的环节。
5
企业的合同应对方案
《民法典》和《九民纪要》的规定,在特殊情形下赋予了违约方摆脱合同的主动权,促使违约方应当承担的非金钱义务向违约损害赔偿的金钱义务转化。
为防止违约方滥用权利,逃避非金钱义务的履行,我们认为,守约方有必要在合同违约责任部分提前筹划,规避实际损失难以界定的风险。
鉴于《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违约金调整”条款,相较于《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给予法院更多“违约金调整”的自主决定权,意味着当事人间事先约定的意定违约金拥有更多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针对性的违约责任条款设计
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对违约方“请求法院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本身约定特殊的违约金,并且不影响其他违约责任的承担。通过这种针对性违约金条款的设计,能从侧面抑制违约方主动寻求摆脱合同。
2) 针对主给付义务设置更完整的违约责任层次
对于非金钱义务,根据不同的违约程度,设置替代履行标准、迟延履行金和一次性违约金等多种违约责任层次,从而在法院判令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后,为原给付义务的履行不能提供相应的、明确的对价标准。
3) 明确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
对于合同的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如提供发票、配合公司证照章交接等,也要提前约定违约金、迟延金等明确具体的违约责任,避免因违约方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导致守约方事后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难以向对方主张。
4) 约定结算和清理条款
根据《民法典》第567条规定:
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因此,有必要在解除条款之外,对已经履行的部分独立制作结算和清理条款,提前对当事人间合同终止后的利益状况作出安排。

6
结语
《民法典》和《九民纪要》的规定,在法律层面为违约方摆脱合同僵局提供了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警惕,违约方的该项权利有被滥用和扩张的风险。为应对违约方逃避原合同义务,守约方损失难以界定的情况,我们建议在合同中预先设置完善的违约责任体系,以期最大程度保障守约方利益。
责任编辑:刘宽